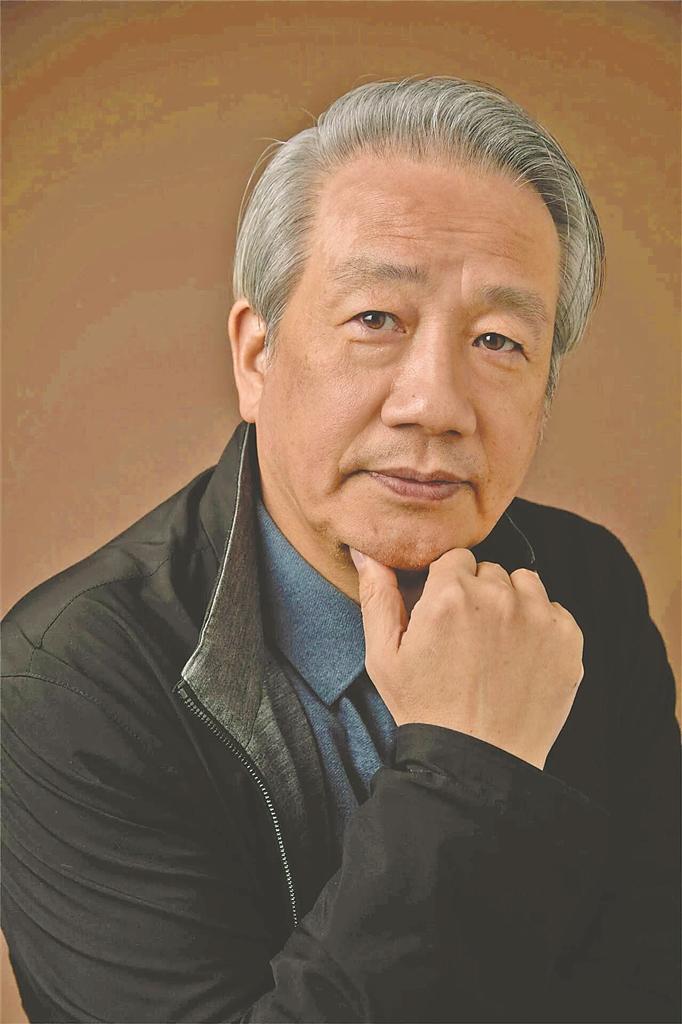
作者生活照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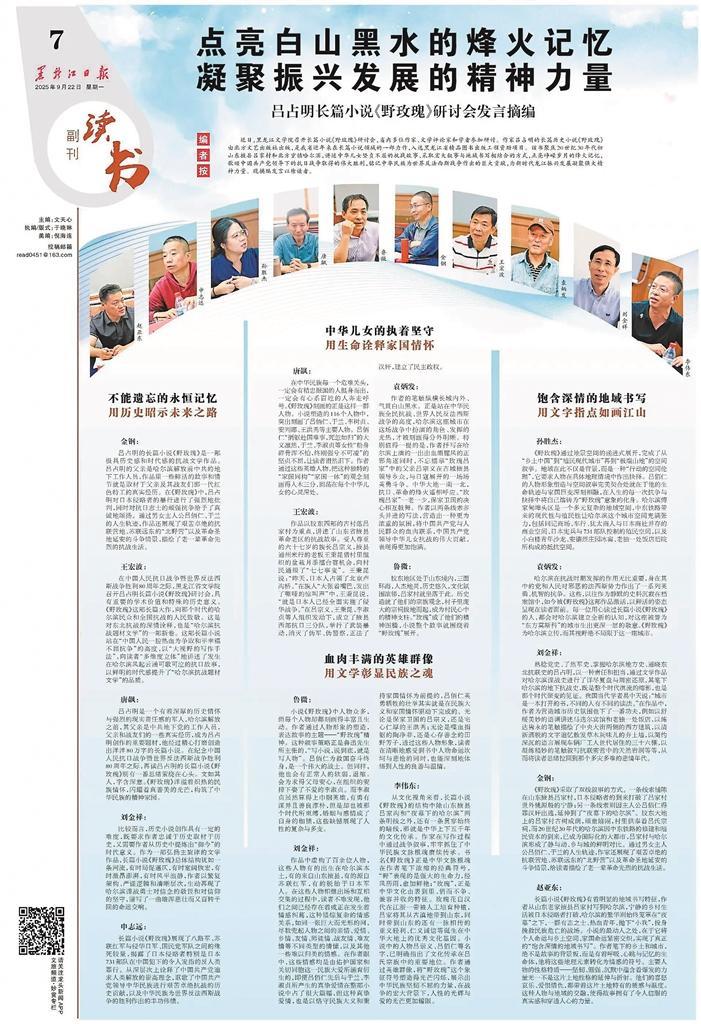
長篇小說《野玫瑰》研討會發言摘編版式圖。
□呂占明
1974年春夜,晚風還裹著殘雪的涼意,父親攥著張《黑龍江日報》跨進家門。油墨香混著他身上的寒氣,在燈下散成一團暖。記得報上印著李兆麟的故事,還附帶著帶歌譜的《露營之歌》,報紙上的個個墨字,亮得像團團篝火。他指著歌詞,慈愛的目光里裹著股沉重:“背下來。”
在此之前,我只在學校的操場上哼過這歌,調子熟稔,詞卻沒往心里去。可那天對著報紙上的歌譜,“火烤胸前暖,風吹背后寒”突然間有了重量:它不僅是孩童嘴里輕飄的調子,更是林海雪原里焐著篝火的詩,是先烈忍著痛在日本人老虎凳上流下的血。父親從沒提過自己做地下黨潛伏的日子,那首歌詞像把鑰匙,撬開了他不愿敞開的口。原來我隨口的哼唱里,藏著他那一代人生死交織的艱辛,藏著刀光劍影的悲涼。10歲的我盯著報紙的模樣,竟成了無法隱去的畫面,一筆一畫刻進腦子里,再也沒淡過。
列寧說,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。這話我后來才真正讀懂,可父親早用一張報紙,把這份信念種進我內心的深處。往后這50年,《露營之歌》的調子沒斷過,父親偶爾漏出的抗爭片段也沒斷過:比如十幾歲的他因送情報被發現,蹲過日本人的大獄,九死一生;又比如戰友為保護情報,被日本人捆上石頭沉進了松花江。這些驚心動魄的過往,仿若給《露營之歌》添上了注腳,總在我的腦海里不停地縈繞。于是便有了后來的我,埋在史料里濃縮出《野玫瑰》,寫抗聯的熱血,寫地下黨的沉默,寫這片黑土地上不曾被忘記的人。
沒想到小說完成后,10位專家的評論,竟被《黑龍江日報》用一整版刊了出來。捧著那版報紙時,我的手止不住地抖。這不是普通的版面,是我從小敬重的黨報,是50年前載著《露營之歌》走進我家的報紙——它把我對文學的追求,變成了對父親那代“沉默者”的致敬。父親走得早,可我知道,他若看見這一幕,定會像當年那樣,指著報紙說:“背下來。”這文字,是獻給所有用生命守護過這片土地的人,也是獻給每個用文字打撈歷史的人。
蹉跎歲月,英靈長存。《黑龍江日報》像兩座橋:一橋架起10歲的我與抗聯的過去,一橋架起今天的我與先烈的未來。我流淚,不是為自己,是為這紙頁里藏著的傳承——它讓《露營之歌》的調子沒散,讓父親那代人的榮耀沒沉,讓百年前的先烈能“看見”今天的盛世。往后我還會繼續寫,像父親當年把報紙遞給我那樣,把這些故事傳遞下去,讓更多人知道:今天的安穩,是有人用生命、用沉默換來的,這歷史,不能忘,也不敢忘。
(作者系作家,原黑龍江省國際友好聯絡會副會長兼秘書長。)
